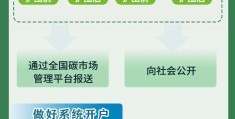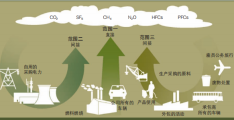潘思佩 等 | 新型城镇化何以引致碳失衡?——基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组态分析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潘思佩
通讯作者:郭 杰
1.潘思佩,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慕尼黑工业大学联合培养,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低碳城市发展;
2.梁加乐,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联合培养,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变化、城乡发展和管理。

更多资料,添加微信
复制微信号
3.陈万旭,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化资源环境效应,人地系统转型;
4.郭 杰,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与管制、景观生态与可持续性科学;
5.欧名豪,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全文刊发在《中国土地科学》2024年第12期(点击可查看当期目次和摘要)
能源消耗增加和人口不断增长显著加快了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2010–2016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收量仅为当期人为碳排放的45%,意味着存在巨大的碳失衡问题。全球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背景下,城镇化依旧是碳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转型的关键时期,未来30年城镇化率仍有20%的增长空间。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对碳源的影响,对碳汇功能变化的探讨相对较少。这种单一视角难以全面揭示城镇化对碳平衡的复杂作用机制。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涉及多维度因素:人口城镇化(POP)、土地城镇化(LAND)、经济城镇化(ECO),社会城镇化(SOC)和生态城镇化(GRE)。传统线性分析方法难以捕捉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因此,从组态视角分析新型城镇化引致碳失衡的影响机制,能够有效应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多重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全面实施的重要标志。2016年,十三五规划(2016–2020)将“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明确提出要以都市圈、城市群为载体,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自此,新型城镇化的重点转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和地形地貌的差异形成了资源要素的初始势能差,一定程度上是东中西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的典范。因此,以三大城市群作为典型代表,从组态视角揭示新型城镇化如何引致碳失衡,有助于为我国城市群制定差异化低碳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支撑。基于此,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1)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哪些组态路径引致碳失衡?(2)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怎样的路径空间分异?(3)如何根据不同的组态路径,制定差异化的城市群低碳发展策略?
研究从组态视角出发,考虑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对城市群碳失衡的影响,从复杂社会现象中剖析出多因并发的复杂因果关系,从而为低碳城市群发展提供新视角。首先,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区,在市级层面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测算碳源和碳汇并计算碳失衡状况,最后运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揭示新型城镇化引致碳失衡的组态路径及其空间分异性,基于此提出差异化的城市群低碳发展策略。
(一)必要条件分析
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均不构成碳失衡的必要条件(均<0.9),即新型城镇化任一子系统都不是导致碳失衡的必要条件,说明新型城镇化引致碳失衡的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各子系统相互联动共同作用影响区域碳失衡,因此有必要进行组态分析。
(二)条件组态分析
2014–2017年共形成4条条件组态,解的覆盖度为0.58,可以解释58%的案例(表1)。这一时期的组态结果表明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成为碳失衡的主导因素,特别是发展较为迅速的长江中下流区域。2018–2021年共形成4条条件组态,覆盖度为0.57。这一时期的组态结果表明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仍对碳失衡产生影响,但同时,社会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开始发挥重要影响。从全域来看,人口增长并不作为引致碳失衡的核心条件。但无论哪个时期,经济发展都是引致碳失衡的关键条件,但到后期,其更多是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引致碳失衡。
(三)空间异质性分析
成渝城市群2014–2017年主要形成3条组态路径(表2)。其中,Q1表明人口和经济发展是导致碳失衡的两大主导因素。2018–2021年则形成了四类十条组态路径,但主要分成经济发展引致型(H3)和双元主导型(H2、H4)。其中,SOC出现在除了H1以外的所有组态路径中,且大部分以核心条件存在,表明在该时期,社会发展是导致碳失衡的核心因素。
2014–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形成3条组态路径(表3),但主要表现为两大类:ECO-SOC双元主导型(Q1)和不相关型(Q2,Q3)。其中,ECO-SOC双元主导型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导致碳失衡的主要驱动因素。2018–2021年则形成了6条组态路径,出现了独特的社会发展引致型组态路径(H2),但不相关型在前期还是后期都存在,也解释了碳失衡并不全是新型城镇化导致。
长三角城市群2014–2017年主要形成4条组态路径(表4)。除了城市扩张引致型(Q2)、经济发展引致型(Q4)和POP-LAND双元主导型(Q3)外,还出现了独特的人口引致型(Q1)。2018–2021年期间,LAND作为核心存在条件出现在多数组态路径中,且多以唯一核心存在条件引致碳失衡(H2、H3)。但这一时期,组态路径更为多元化,共形成了11条组态路径。
“双碳”背景下,揭示新型城镇化引致碳失衡机制,对于促进中国城市群的低碳转型发展极为重要。研究发现:
(1)新型城镇化任一子系统都不是导致碳失衡的必要条件,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引致碳失衡内在机制的复杂性。
(2)尽管城镇化发展导致碳失衡的组态路径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且导致碳失衡的条件组态在后期比前期更为多样,但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是导致碳失衡的两大主导因素,社会发展则在后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口城镇化则多以与其他子系统共同作用导致碳失衡。
(3)区域差异分析表明,成渝城市群的碳失衡在前期主要以POP-ECO双元主导型为主,后期则转变为以ECO-SOC和GRE-SOC这两大双元主导型为主。长江中游城市群导致碳失衡的组态路径在整个研究期间都相对其他两个城市群少,前期以ECO-SOC双元主导型为主,后期则转变为LAND-GRE双元主导型。长三角城市群引致碳失衡的条件组态最为多样,但多为单因素主导型,尤以城市扩张引致型最为突出。
研究结果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引致碳失衡的组态路径差异,强调了城镇化进程中采取差异化措施促进碳平衡的重要性:
(1)对人口流入较大且城市扩张较为显著的长三角城市群,前期人口因素通常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引致碳失衡,后期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对于该区域控制碳失衡的关键在于控制建设用地扩张,推动紧凑型城市发展。通过设立城市增长边界防止无序蔓延,保护周边生态环境,提高碳汇能力。同时引导城市在现有边界内进行优化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市高密度开发和多功能区划,减少城市交通需求,降低因城市扩展带来的能源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
(2)对于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向成熟阶段过渡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引致碳失衡的组态路径较少,但经济和社会发展是重要动因,生态城镇化的作用也开始凸显。因此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绿色低碳产业转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智能制造、节能减排等技术的发展,从根源上减少碳排放从而实现碳平衡。同时通过持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城市绿化和生态农业,遏制围湖造田等破环生态环境行为,提升区域碳汇能力。
(3)对于正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的成渝城市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是引致区域碳失衡的主要因素,因此应重点发展绿色交通、智能电网等低碳基础设施,降低城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同时引导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变,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环保意识,鼓励低碳消费模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本文责编:陈美景;网络编辑:曾 爽)